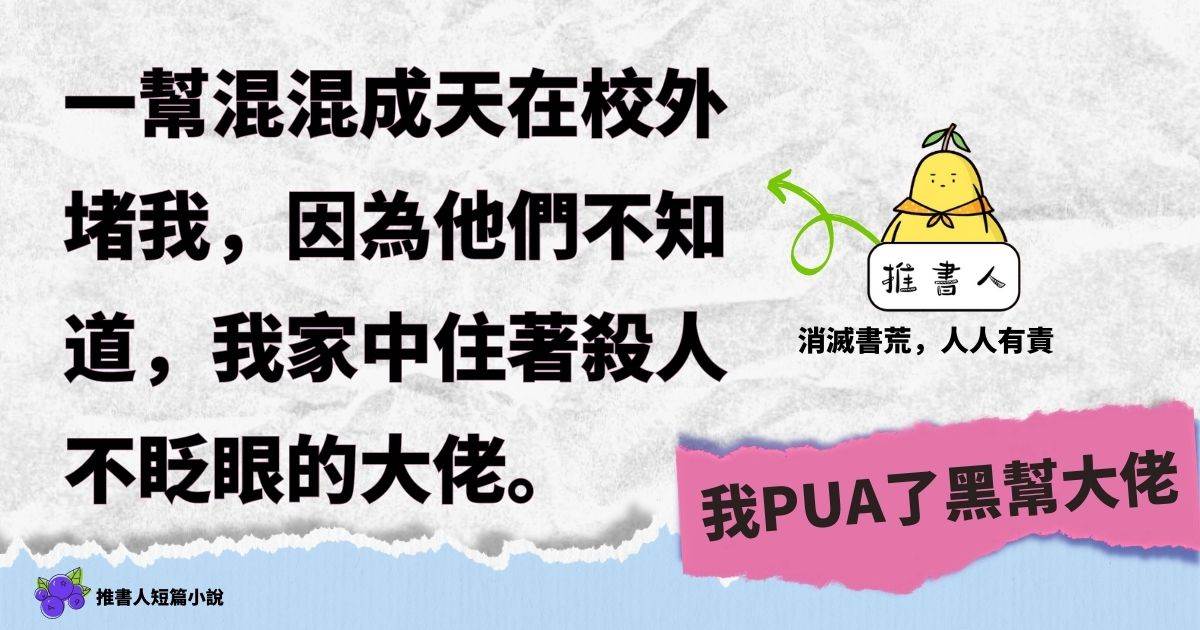《我PUA了黑幫大佬》第11章
」
我目光轉而堅決:「我有一個想法,讓程安洗白做正經生意,讓他跟我一起過正常的生活。我大學學的金融,就是為了日后幫他走上正軌。」
白獅松開我,拍了拍手,冷哼一聲:「那你還幫他走私,這不是自相矛盾嗎?」
「他說這筆錢對他很重要,我的計劃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。在這之前,我只希望程安平安。」
白獅背對著我沒吭聲。
我心底落下一塊石頭,繼續道:「白獅大佬,在港市只有程安能與你制衡,假如程安不再做這些生意,那港市就是你獨大。難道于你于我而言,不是雙贏嗎?」
白獅轉身,目光不再似之前那樣兇狠,多了一絲玩味。
「你確信程安能聽你的?」
「能!」我態度很堅定:「程安愛我,而且,他真的只是一個單純的人。我相信,我一定可以讓程安回歸正常的生活。」
「你知道他手上有多少人命嗎?回歸正常人談何容易,且不說生意是否能洗白,想要做正常人,最少要坐幾十年牢。他手下那麼多兄弟要養,會為了你不顧一切,未免太自信。」
「他坐牢我就等他,我還可以為他打官司,爭取減刑。港大的金融專業每年只招五個人,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關注,港市在走向新經濟發展,有很多合法掙錢的產業,股票,房產,勢頭正猛,都會是后起之秀。我學成出來定不會差,我會帶著幫派做正常生意謀生,讓大家有可靠的工作。沒有什麼能阻擋我。」
我一直仰著下巴與他對視,滿是堅決與無懼。
大概有兩分鐘沒有說話。他忽然哼哧一笑:「還真是小瞧你了。
ADVERTISEMENT
」然后他解開了我的繩子,威脅的語氣:「我就信你這一次,若所說有假,你會死得相當難看。」
我揉著手腕:「多謝白獅大佬。」
程安也在這時趕到,出去后。我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氣,幾乎癱在他懷里。
程安怒火中燒,咬著后槽牙:「白獅,你他媽做了什麼?」擼起袖子就要開干。
我拉住他:「白獅大佬只是找我來說一下去緬國的注意事項,沒有為難我。」
程安不信,我把臉埋進他的胸口,低聲道:「我想回家,程安哥。」
他這才罷手,抱著我上了車。
15
我急切地問徐奶奶怎麼樣了,程安說他趕到的時,救護車剛好走,此時應該在醫院。
我想去醫院,被程安制止,說那邊很混亂,應該有不少警察在交涉,讓我明天再去看望。
他詢問我有沒有受傷,嘴里一直在怒罵白獅。
我一直安慰他沒有自己沒事。
現在我渾身還在冒冷汗,平靜之余是后怕,幸得我演技和心理素質扛過了白獅那雙鷹眼。
好險,好險···
程安說什麼都不放心我再一個人住,讓我搬到他的住處,上學讓保鏢接送。
還有半個月就開始行動,我同意了。
只是第二天,傳來噩耗,徐奶奶去世了。
我去了醫院,只見著冰冷的骨灰盒。他們家里人對警察都宣稱的病逝,但是那一雙雙紅腫的眼睛騙不了我。
他們是惹不起白獅。
我默默走出了醫院,心痛得無法呼吸。那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,我不知道怎麼走到的別墅。
這幫人可真該死啊,都死才好。
后面病了兩天,程安衣不解帶地照顧我,給了一張五十萬的卡,讓我交給徐家。
ADVERTISEMENT
我把這筆錢交給了周宴欽,讓他查一查是否干凈,然后轉送給徐家。
是干凈的。
出發前我去看了外婆,剛好是國慶節。
程安帶上了三個心腹,加上我四個。
白獅也人數同樣,還有黑皮。
我們坐的是私人輪渡,上去前所有人例行檢查,除了程安和白獅。
我身上只有程安給的一把槍,甚至沒有手機。
看見黑皮,我就忍不住捏緊槍,要說服自己半天才能冷靜。
夜晚黑皮把我堵在角落挑釁:「那老太婆死了,是不是很氣?」
我要走,他又抓住我:「臭婊子,你就是個窩囊……」
下一秒,他直直撲了出去,頭撞在船壁上。程安冷漠地走過去,對著他又狠狠踢了兩腳。
「做什麼?」白獅滿臉不悅過來。
程安拉著我走,擦肩而過時,冷聲道:「管好你的狗腿!」
我安撫他:「程安哥,我們都在一條船上,別傷了和氣。」
程安哼了一聲:「狗東西,回去老子干死他。」
下了輪渡,又坐了五個小時車到達緬甸。
其實坐飛機要不了這麼久,但是他們一路沒有遇見過檢查的人,這是在繞路。
到達緬甸,他們并沒有立即去到交貨,而是在街上晃了又兩天左右。
程安帶著我買了各種有意思的花樣,吃了好多東西,還看了馬戲團。
一路上,我都有發現,其實有便衣警察在跟蹤。他們在玩貓捉老鼠。
第三天,我們坐著小轎車出發,但是兩邊都少了一個人。
我沒問來由,默默觀察。
一路上很偏僻,都是灌木叢林,路行曲折,沒有人煙,像是沒開發的原始部落一般。
我們到了一戶人家,是個緬人。
程安和白獅在外面與他交談,同時扛了四大袋沉沉的東西到車上。
程安說過,最大的老板是美國人,所以這個不可能是白粉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